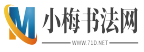大小:
下载:553次
分类:书法访谈
手机扫码免费下载
纠错留言#唐睿宗书法《景龙观钟铭》研究简介
景云钟因铸成于唐景云二年(711)而得名,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钟为铜、锡合金,重约六吨,口沿为六角弧形,顶端置“蒲牢”钮,中下段正面铸有铭文共十八行,二百九十二字,由唐睿宗李旦撰文并书。铭文内容大致可分为“道教一些神秘的意识和景龙观的来历”、景云钟的制作过程及铭词三个部分。曾因此钟放置于唐代长安城景龙观钟楼,古代著录多称为《景龙观钟铭》(以下简称钟铭)。《述书赋注》说唐睿宗书作“规模尚古”;《石墨镌华》形容此铭“奇伟可观”;绍基《东州草堂文钞》说钟铭乃睿宗代表作,更是视其为“唐迹中难得之品”;《大瓢偶笔》又谓此铭“古奥浑厚绝非他碑可及”;刘熙载《艺概》则注意到,此铭体杂糅,乃效东魏《李钟璇修孔子庙碑》与隋《曹子建碑》,但“颇能节之以礼”。最有意思的是《铁函斋书跋》说此书“沉郁古奥,为东坡之祖”;郭尚先认为此“以分隶为真书”且“气象雍穆”。由此可见,历代学者对此铭的书写多持肯定态度,也给他们留下了“古奥”“雍穆”的印象。1《新唐书》也曾载,唐睿宗“温恭好学,通诂训,工草隶书”2,他可以说是唐代帝王中的善书者了。其见之于世的书迹不多,除钟铭外,尚有《武士彟碑》、《顺陵碑》《武后述志碑》(另称《升中述志碑》3)、《孔子庙堂碑额》等可从文献记载中见知。其中《顺陵碑》原石先被万历乙卯(1615)一场地震所断,后又被用作修砌河岸的石料,幸有明中叶未毁前拓本传世,为我们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唐睿宗书迹面貌。4相比《顺陵碑》而言,对钟铭的研究和关注则可谓寡见。长期以来,除少量的古代著录和简略的风格叙述外,对其书写及相关问题尤乏深入研究。5笔者因偶然的机遇,开始对钟铭有所关注,并对其书写风格及历史背景饶有兴味,觉得与钟铭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应当还有余话可说,所以不揣浅陋,拟述浅识。

=01=镜堂藏《景云钟铭》拓片
就已有的著录和评述来看,对于此碑之书写问题的关心大多集中于明清两代,查宋元文献,少有述及。《山右丛书》初编载乾隆四十三年,汪日炎校刊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另附宋振誉《补遗》一卷6,此卷内容主体为“乾隆六年杭郡宋振誉补其家之所藏”,其中就有《唐景龙观钟铭》一篇,后有跋语道:
右铭字正书而稍兼篆隶,奇伟可观。钟今在陕省城钟楼,拓之甚难,故都工不及收也。7
都氏著作因何未收此拓,且世间流传极少,宋振誉的解释是:钟楼高而不便拓取。关于这个问题,后世题跋多有述及,景云钟自明代洪武年间移置迎祥观钟楼,悬于十丈之高,自然不便捶拓者操作。又有一说,钟楼近邻臬司,衙门“恐拓印者下窥官舍”8,索性禁止登楼。时日既久,钟铭逐渐被人淡忘而敷上一层神秘色彩。当时普遍认为,钟铭拓本有“镇邪”之功,尤其朱拓本,可以避水火、怪风9。可以说,从世俗角度而言,“其辞典雅可诵”的文辞,“古秀圆劲,寓篆隶于楷法”10的独特书写并不重要。钟铭拓本在晚明以来才开始逐渐传播,且朱拓本尤为收藏者热衷,最初的原因是景云钟”的宗教性质比较符合民间的需要,其次当是椎拓条件的改变。王翰章《景云钟的铸造技术及其铭文考释》及罗宏才《唐景云钟诸种拓本与相关问题考论》等少数关于钟铭的研究成果,对钟铭的基础信息及拓本流传等问题做了详尽考述,为我们研究钟铭的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1,而钟铭本身的历史及其书写中所隐含的意蕴尚待深入挖掘。
一
关于钟铭的书写者,似乎少有人质疑。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认为钟铭虽没有明确署名,但依前说,基本可以确定为唐睿宗御书亲笔:
铭文中有“朕翘情八素”的句子,文末的纪年为景云二年(711)。与睿宗御书的《孔子庙堂碑》及《顺陵碑》额比较,其字体完全相同。因此断定此铭为睿宗御书,这一点前人已有定论。12
虽然铭文中有“朕翘情八素”这样明确的主语,但也不能就此“断定”钟铭是“睿宗御书”。《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中存在大量类似的主语,而书丹及摹勒者非其本人,这样的情况,在帝王书碑中并不鲜见13。足立喜六“与睿宗御书的《孔子庙堂碑》及《顺陵碑》额比较,其字体完全相同”一语,存在明显的表述错误。首先《顺陵碑》不见碑额,有“碑额”的当为《孔子庙堂碑》。据史载,此碑原石建立后不久即遭损毁,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命相王李旦(睿宗)重刻,确有李旦题额,惜唐末再遭毁佚。今所见此碑拓本都是宋以后重刻14,今存《孔子庙堂碑》碑额是篆书,已无法与钟铭对勘15。
另外,《顺陵碑》今存残石五块,故称“顺陵残碑”,有上海博物馆藏“宋拓全碑孤本”及陈清华藏“明拓未断本”两种。碑帖版本专家仲威将前者与“残石本”并看发现,两者并非同出一石,“全碑本”为后世翻刻,翻刻的底本确出于明代之前的拓本16。今存海外的陈氏藏“明拓未断本”,后有翁方纲、孙星衍、何焯及褚德彝等人的题跋,都未曾对此拓提出质疑。17难以提出质疑的原因或许有二:一是没有可资校勘的睿宗传世墨迹,二则当时见到残碑拓本已属不易,更不消说未断时的其他拓本。这一点从孙星衍及翁方纲两人在陈氏“明拓未断本”上的题跋中可以看出:
嘉庆壬申岁五月,子千子出示此碑,惊以为海内无第二本,属钩摹上石未果。衍刻续古文苑,多取书传缺载之文。得汪氏士铉手书唐碑一册,内有此刻,急刊入集。今校是册知阙数百字,非赖退谷手迹,后人竟无从补完矣。仍据分重雕上石,以存妙迹。其文字佳妙,自不待言。孙星行书。18

=02=陈清华藏“明拓未断本'局部

=03=《顺陵残碑》拓本之一
孙星衍一见朋友送来的拓本,则惊为“海内无第二本”,当然是未曾见过全本。翁方纲虽然藏有残拓,但尚没有收集五块残碑拓本的条件:
闻咸阳县廨此石尚存二片,予藏其一是淡墨拓者。19
既然没有准确的比较,就很难判断优劣与真伪,更难以确定书迹出自何人之手,所有的结论,似乎只能来自对文献的信赖。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感觉到,足立喜六所作出的“明确”判断尚有存疑的可能。周退密在《<唐顺陵碑〉残石旧拓本题记》中就对此碑书写者是否为睿宗表示过怀疑:
此旧拓唐顺陵残碑剪贴本,与所藏整幅者墨色相同,当为同时所拓,常以之悬诸壁间作竟日观。传此碑为睿宗御笔,未必可信。初唐人书除欧、虞、褚、薛之外当推此刻,所谓“骨寒神秀”是也。20
由这段跋文看来,周退密此前还藏有残碑的整幅拓本,并悬挂壁间时时赏玩,可见对此碑十分珍视。一方面因为残碑本来珍贵;二者,虽然不能断定此碑确属睿宗所书,但此碑的书写水准确实让他心仪。在没有见过睿宗其他书迹的情况下,提出质疑也是情理中事,抑或从拓本间发现某些蛛丝马迹,只因不能列举确证而止于初步的提出疑问。
褚德彝在陈氏“明拓未断本”上的题跋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
……此本乃未坏时所拓者。观其纸墨深古,定为宋代遗物。……考宋《宝刻类编》,此碑下注长安二年六月,今拓本作长安二年岁壬寅金玉“玉”即武后新制之“正”字。知此碑在宋已有缺泐,故以“正”讹“六”,更可证其为宋世毡椎也。睿宗书《金石录》载有《升中述志碑》,在嵩山,政和中为守臣所碎。又《武士彟碑》,今皆不存。《景龙观钟铭》及开元刻《孔子老子赞》,仅数百字,均不能与此碑并论。……今此碑用笔遒丽雄伟,气象万千。辈几风规,去人未远……21
对于此本椎拓的年限,褚氏因其“纸墨深古”论定在宋代,显然缺乏十足的根据。在他看来,钟铭等其他遗迹字数太少,规模与此碑不可相提并论,并由此而推测,窦臮《述书赋》中对睿宗法书“飞五云而在天”的形容正来源于此碑。至于“用笔遒丽雄伟,气象万千”之语,则难免流于修辞而无实际意义。关于此碑的书写者,翁方纲及褚德彝的题跋中都因资料所限而缺乏立论的根据,往往只能寄托于直观感受与文献相对应,而周氏提出质疑的根据也无从考证。
笔者以仲氏所举“宋拓全碑孤本”与陈氏藏“明拓未断本”图片相比较,两者十分接近,只是前者残损更多。另外,以上两种版本与残石拓本相比较,突出的差异就是肥瘦问题——前二者肥润,后者枯瘦细劲(见图02、03)。这些差异对于碑刻书写者的判断都无重要意义,因此,对于钟铭为睿宗所书的“定论”很难进行辩驳。但从体势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钟铭与《顺陵碑》各版本的书写出于同一类风格。而足立喜六所谓的前人“定论”,实际上也不能作为判断钟铭就是睿宗所书的有力证据。

=04=《升仙太子碑》示意图,见唐雯:《女皇的纠结一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政治内涵重探》,第230页。
唐代帝王碑刻的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参与的人数众多。帝王与碑刻之间的关系,往往要借由一位善书者摹勒及刻工的镌刻而呈现。关于这个问题,叶昌炽在《语石》中早有论及,王昶也认为“凡御书碑,皆有‘敕、使’二人,即负责检校与摹勒的专门人员”。而叶昌炽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唐代御书碑都会明确记载这些司职人员的姓名,像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中那样详载参与人员的御书碑刻并不多见,因而认定这种现象并非为当时通例。22 据学者研究可知,睿宗书《武士彟碑》,确由崔知之摹勒上石,23 而非亲笔书丹。钟铭铸造的工序远比墓志的制作复杂,其间必然经由模书人之手方能顺利完成。试想,身份尊贵的睿宗皇帝必不会亲临铸造现场,并手书成范。如果钟铭也如《升仙太子碑》那样为"奉敕勒御书”,既然是经过摹勒的过渡程序,则必然在细微的形式上有所呈现,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论。
此番杂述,不意推翻前人定论。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能确定钟铭为睿宗手笔,则意味着将相关文献叙述与钟铭书写风格联系起来讨论,难免有海市蜃楼之感,难以切实进入真正属于唐代睿宗时期书写风格的讨论。另外,古代书写风格史研究,往往会遇到一种困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讨论一件作品与某人的关系,或许这件作品与此人并无实际关系,这时,用于讨论的文献则在顷刻间沦为无用之物。因此,必须将作品本身作为展开研究的最重要材料,每一个被发现的细节都不能错过。如此深具政治意义的书写工作,自然只有得到了睿宗本人的认可才得以开展。且不论钟铭的具体书写者,而其书写风格至少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宫廷书写趣味,及其对风格的选择。对钟铭的内容及书写风格加以细致地分析,或许能增加对这一时期主流书写观念及具体实践的认识,为唐代书法史研究确立一个新坐标,借助它研究初唐书写观念的变迁,为唐代书写史研究提供一条线索。这也是对钟铭的历史及艺术价值作出更新、更准确判断的契机。
二
从细节看钟铭的书写者
桑椹《朱拓唐景龙观钟铭拓本册》一文认为,清代前期古物出土数量不多,书家只能从有限的金石材料中揣摩“古意”,理解失于偏颇在所难免。道、咸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勃兴,这种现象有所改观,这可以从人们对《景龙观钟铭》书法评赏方式的微妙差异中见得。若以清代学者的标准来看,钟铭的书写“尚是‘姿’有余而‘骨’不足,风格总体上仍归于‘媚’的一路”。24 另外,桑文所使用的钟铭“傅绳勋藏本”后有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何元锡(1766—1829)之子何溱(1791—?)的题跋,共六开半,除摘录前人评述外,另有自作一跋,内容概括了初唐及睿宗钟铭的书写风格:
初唐人书上承六朝,气脉自有一种清劲之气,显然可寻,非后世所能几及!首行与末行“一”字,八行“之”字,十四行“上”字,均是飞白体,迨所谓飞而不白者欤?观《升仙太子碑》飞白书,颇可悟此意。25
何溱的题跋关注到钟铭书写的特异之处,具体指出了“一”“‘之’”“上”等字“飞而不白”的现象,及其与《升仙太子碑》碑额飞白书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惜未能对此作深入的阐释。笔者在未见何氏题跋以前,对这一现象也十分好奇。两件书刻背后复杂的历史关系,不由得使人产生各种联想。
钟铭“之”字具有装饰性的写法,很容易使人与武则天的飞白书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飞白书自隶书发展而来,起初是为隶书大字题写匾额的“审美调节”,但发展到唐代,飞白书的书写工具发生了改变,这是“飞白书艺术开始沦落”的标志;武则天又将“鸟形”融入其中,使其变而为一种文字游戏。26从陆文援引的文献来看,飞白书中的飞动之势始终是这一书体形式演进的根源。将飞白书兼容鸟形,恰合飞动之势27,似乎合情合理。《升仙太子碑》碑额中的点画不仅形状为鸟形,且其“头部”点有睛目,显然不是一笔写成,其过程或同于绘画。28将它和唐太宗《晋祠铭》额“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唐高宗《大唐纪功颂碑》碑额相比较,武则天飞白书中“鸟形”体态丰满,形状生动,制作时明显有突出“鸟”这一符号的心理动机。这种在文字本体以外饰以鸟形的做法,不禁使人联想到始于远古的鸟虫书。鸟虫书的构形方式,不仅有将鸟形寓于笔画之中的,也有将鸟形作为一种纯粹的装饰外加于文字本体的。而鸟虫书的诞生,本身即出于对文字形态的装饰,反映了某种审美意识潮流,并非文字表意系统所需。29最早的鸟虫书,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装饰性与象征性,正好用于旗帜符号的装饰30。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记录了当时文献所载诸种书体的由来,对于鸟虫书的成因,韦氏的解释是:
周文王时赤雀街书集户,武王时丹鸟入室,以二祥瑞,故作鸟书。31

=05=《升仙太子碑》碑额

=06=唐太宗《晋祠铭》额

=07唐高宗《大唐纪功颂碑》碑额
将书体与这类传说联系起来,增添神秘感的同时,更是重申文字在古代社会所承担的教化功能,以及对文字符号的诞生与一代圣君之间必然关系的强化。无独有偶,武则天“革命”之初,为制造其权力合法化的逻辑,32有意将武氏一族的谱系上溯到周文王,并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尊周文王为文皇帝,武王为康皇帝。武氏登基,陈子昂旋即上表称颂,颂表有云:
“凤乌不至,河不出图,邱已矣夫!”……今者凤鸟来,赤雀至,庆云见,休气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33(《上大周受命颂表》)
……凤鸟从南方来,历端门,群鸟数千蔽之。又有赤雀数百从东方来,群飞映云。……况凤者阳鸟,赤雀火精,黄雀从之者土也。土则火之子,子随母,所以纂母姓。天意如彼,人诚如此,陛下曷可辞之?昔金天凤凰,镐京黄鸟。赤氏朱雁,有吴丹乌,皆纪之金册,藏之瑞府,以有事也。陛下若遂辞之,是推天而绝人,将何以训?34(《大周受命颂》)
在陈子昂的两篇文章中,多次提到“凤鸟”“赤雀”和“丹乌”,并附会这些祥瑞为武氏践祚的神符。对于武氏而言,这无疑为其构建自身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陈氏也因这一举动,遭到后世文人的诸多非议。宋人陈振孙称其“纳忠贡谀于孽后之朝,大节不足言”的同时,又说他的诗文“在唐初实首起八代之衰”35。陈子昂果然精通文学描述,巧妙地将象征周文王的“朱雀”和象征武王的“丹乌”,以及象征武后的“凤鸟”作为颂文的重要元素,制造神鸟翔集的瑞应图景,大肆渲染武则天“子随母”与“纂母姓’的合法性。此时,武则天也已开始她的造字工程,以期从文字阅读和书写上强化意识形态的统一,正如《宣和书谱》所言“自我作古”36。她一改“日”字旧形,将“鸟”的形象放置于圆圈之中,以此配合“惟我有周,实保天德”的舆论形势。当她为《升仙太子碑》题写碑额的时候,不仅选用了象征着周文王和周武王“圣德”的飞白体,而且还着意强化百鸟朝凤的视觉意蕴,此中深意自然明矣。现在看来,韦续关于“鸟书”生成史的叙述,确因其“荒渺”而“不足信”37,但武则天借题发挥以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历史,却可以通过“荒渺”的文献窥探些许。“子随母"这一概念的生成,使得唐中宗及睿宗两人的位置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睿宗还是王子的时候,就经常被其母武则天委任书写大型的官方碑刻,尤其是为其外祖母的陵墓书写纪念碑。这既是颇具感情色彩的仪式,也是宣示政治取向的信号。通过对《顺陵残碑》及钟铭的综合考察,睿宗书写中的一贯性,正是武氏造字等“复古”行为的一种反映。
当睿宗书写钟铭时,武后所造的新字已经全面停用,而铭文第八行的“之”字两处都完整地保留了武氏笔下那丰满而生动的“鸟形”特征,其他六个“之”字却又保持着常态的书写。另外,何溱所提出的“一”和“上”两字的横画,笔意出自隶书;但其加粗笔触,使横画显得短促,加上隶书的波折,正好与鸟雀的身形相吻合。这一细节,不得不引起注意。
除此外,钟铭里特异的书写细节不胜枚举,从下面的图表即可看出。据统计,钟铭共292字,其中具有异体字及其他奇异特征(有别于唐代楷书的常见书写形态)的有四十余字,所占比例较大。其中既有篆、隶笔意,也有多个单字直接使用篆书的部件,有些单字直接由篆书和楷书两个部件构成。譬如“控”“道”“有”“教”“耶”“超”等字就属此类,但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楷书化。另如第一行“一”、第二行“而”字首笔、第七行“晋”字首笔及第十四行“上”字末笔,却直接保留了隶书笔画的特征(见图08《异写字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如前文所谈“之”的现象——相同单字多次出现时形态上存在的微妙变化。“之”字在整幅中出现七次,除第八行特异字形以外,其他六个基本可以归纳为一类,且形态和笔意十分接近。“而”也出现七次,除第二行“而”字首笔作隶书笔型外,其余也基本相同,但相同之中又略见小异。

=08=《异写字表》

=09=《同字异写表》

=10=“聋”与“闻”
钟铭中的三个“韵”字中,以第十一行那个为特异,“音”字上部的“立”部作“大”字底下一横状,显然是篆书结构楷化的通俗写法。其他两个“音”字构建与第十行、第十五行的“音”字如出一辙(见图09《同字异写表》),横向笔画的倾斜度极为一致,这与“之”横画角度的细微变化形成有意思的对比。第十一行“聋”字上部的“龙”与第三行“龙”字也如出一辙;下方的“耳”部与十二行“闻”字内部构件的写法与体势也极为相同(见图10)。在第八行、第十二行及第十三行中分别出现的“宝”字,从“贝”部来看,前两者区别于第三字:从“贝”以上部分来看,第一和第三字区别于第二字(见图09)。这让人感觉到,书写者有意利用不同位置的细微差异,将相同的三个单字形态区分开,这种做法可谓用心良苦。第四行“所”字右“斤”部首笔有明显的篆书笔意,其他部分保持楷书写法;第六行“斯”字及第十五行“新”字“斤”部虽有前者的意蕴,形式上却更接近楷写,两者形态几无差别。另外,这三字左右两部分之间形成一种奇特的关系,从笔意来看,两部分间失去了明显的连贯性。如将此三字左右两部分各画一条轴线,很快即形成三个完全不同的造型,“所”字呈正梯形,“斯”字呈平行四边形,“新”字则呈倒梯形。如将“斯”字与同篇两个“其”字并列,一方面都是异体字的写法,另一方面两个“其”字的轴线都向左倾斜,而“斯”字中的“其”部轴线却明显向右大幅度倾斜(见图08)。这一细微的变化,显示出这几个字可能不属同一时间内的惯性书写,既找不出具有同一性的书写规律,同时也看不到相对整体的变化机制。如果钟铭不是经由第二人拼凑组合而成,那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必须要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始终以十分自觉的心态处理单字形态的变化,“变化”的意识必须时刻贯穿于书写过程。

=11=《最云钟铭》第六行

=12=《最云钟铭》十三行
更多“奇异”的感觉在行的关系上也有充分体现。为方便分析,我们将第六行和第十三行从整体中切割出来观看(见图11、12)。第六行前段的平和状态从第六字开始被打乱,“鼓"字的向右倾斜开启了这一整行的诸多变化,“延”字几乎撑满了整格,主体部分向左倾侧,使右边留出大片空白;接下来的“铸"字回到中心轴线。连续四字的轴线组合成明显的“S"形,这种形态的轴线在整行的中段反复出现,直到最后三字,又回到起初平和的状态。带着这种感受看第十三行,似乎在相同的处理方式下完成。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拓本的整体,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呈现出来:每一行的轴线“S"形变化基本都在这一行的中段展开,相比之下,上下两端都显得平和。另外,从拓本可以看到,因为细线的不规则而导致界格的大小产生细微变化,多数单字自能在有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里安排相应的单字。当摹写第十一列第五字“虡”及十三列第六字“虞”时,没有考虑到界格空间发生的变化,导致文字下部空间十分逼仄,显得极为窘促(见图13)。而“虞字上方的“考”字却因界格的空间变大而写得十分放松,“虡”字上下的“钟”字尽管笔画繁复,却也显得宽绰有余。当我们看到景云钟铸有钟铭部分的照片,实际上书写的平面除固定的弧形以外,其表面也并不平整;相比处理好的石碑表面,钟身表面的凹凸不平则很不易于流畅的书写。界格细线的细微差异,与钟身表面的实际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弧形而凹凸的表面确实也不便于直尺的使用。摹书人将精心准备的文字勒上去时,画好的界格无疑成为书写的障碍。除第八行“节”字超出界格下端外,其他单字都竭力地被安置于界格之内。试想,唐睿宗在纸上书写之时若已有界格,则不可能出现界格大小不均的情况;若无界格,则必然在摹勒时改变原有的组合关系。

=13=“虞"字与“虞"字

=14=钟铭实景图 张志承摄
难怪何绍基在阅读此铭时,因为发现其存在“弱冗”之处,明显与其“奇伟非常”的论断有所冲突,于是将不令人满意的原因推给了制作泥范的工匠。38何绍基所谈论的,仅仅是少量的弱冗,并未能作出全面的分析。我们通过钟铭书写的细节考察,发现其统一部件在不同单字上的借用与挪让,相同单字在同篇出现时有意的形态变化,还有字间关系变化的雷同及其相互冲突,让我们联想到一种可能:钟铭不仅非睿宗亲笔所书,且整幅钟铭的书写,都是由宫廷勒书手依据睿宗旧迹进行的二次书写。这与《怀仁集圣教序》《升仙太子碑》的操作方式十分接近。一个看似平常的钟铭,其制作的背后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身影,他们的通力合作,精心选择那个时代的重要信息,将它们组合并希冀由此向世人展现唐睿宗“奇伟非常”的形象。
古意:书体杂错的钟铭
钟铭的书写集合篆、隶和楷书的形式要素,并将其熔冶一炉。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谈道:
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遗意,正书之中往往杂出篆体,无论欧、虞诸子,即睿宗书亦如此。犹之初唐律诗,稍似古风,平仄不尽稳顺。开元以后,书法日盛,而古意遂亡。遂以篆、楷为必不相通,分为两部。……诗篇书法日以圆熟,而俗笔生焉,亦世道升降之一端矣。39
顾氏这段跋语从睿宗钟铭出发,赅要地总结了初唐的书风之变,并将其与同时代诗文风格的演变相比较。他赞赏“不尽稳顺”却尚存“古意"的初唐书风,对开元以后的日渐“圆熟",态度与前者截然不同。他还细致地观察到开元以后的书写存在楷、篆两个笔意系统的分离,这是阻断“古意”延伸的重要原因,并认为书写风格的递变往往与世道的升降存在密切的关系。既然两者互为映衬,那“古意”在初唐的书写中得以留存,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钟铭》,犹带篆分遗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40
唐代初期的考试制度和内容促进了小学的发展,尚在童蒙的学子们也因此可以接触“篆籀之学”。唐明皇开元以来,先后两次对《尚书》等古代典籍作了增删和御注,对人们理解经典的义理有一定的影响。41随意篡改经典字句和训读方式,实自唐明皇开始。顾炎武对此大加批评,认为“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42。我们可以由顾氏的两段文献得知,他对钟铭书写中所残留的“遗法”十分看重,对于字体杂出的现象颇为欣赏。
相比之下,清代顾堃的见解则大为不同:
《淳于长夏承碑》,其字隶中带篆及八分,洪丞相《隶释》谓其奇怪,真奇怪也。至后魏《李仲璇修孔庙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喷饭。唐睿宗《景龙观钟铭》,楷书也,亦兼篆隶体。宋人《识廨院记》忽楷忽行,又时带篆隶。考古书法,大小篆谓之篆;东汉诸碑,减篆笔有批法者谓之隶;以篆笔作隶书谓之八分,亦谓之隶;正书谓之今隶,亦谓之楷书。各有体制,不得相杂。古人所称隶中带篆籀法者,亦惟用其意而不用其象,故佳耳,岂可以篆隶形象杂出耶?43
顾堃对于字体错杂的现象很不认同,并以“令人喷饭”加以批判。他认为,书体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界限不能模糊;理想的效果,则是巧妙地融合不同书体的意趣。这种见解显然受到术代以降以“意”为之的观念影响,也反映出清代人对于书体界线的泾渭分明,以及书体间相互“融合”的自觉观念。以这种观念为背景,观看数百年前的唐人书写,难免与对象的真实状态存在距离。同一件作品在不同观察者那里产生不同理解,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欣赏和分析的结果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和学术背景。在中国文艺阐释的历史道路上,向来都要依赖文化上的同一场域和默契的建立,才能在心心相印的状态下达成共识44。对于“古意”和“书体杂错”现象的态度,顾氏二人不能达成一致也在情理之中。前者始终关心学术的古今之变,后者则涉及书写中形与意之关系的讨论。对于钟铭书写中的诸体相杂,刘熙载的意见似乎让顾氏二人的“争论”达成“和解”:
后魏《孝文吊比千墓文》,体杂篆、隶,相传为崔浩书。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景龙观钟铭》盖亦效之,然颇能节之以礼。45

=15=《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局部(图片来自网络)
刘熙载简要梳理了这一现象的历史脉络,直接指出钟铭“书体杂错"现象的出现是对前人的效仿,但“能节之以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刘氏对“书体相杂”并不推崇,而不知出于何因,其对钟铭的评价却留有余地。一贯以“中和”之美为追求46的刘熙载,或对钟铭书写中的“礼”存以敬畏。这种纠结的态度颇类欧阳修当年面对“书体杂错”现象的心态。欧氏在收集唐代碑刻过程中,观察到初唐碑刻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风气,虽然对此现象颇为不解,也须聊备一格,甚至坚信自有其存在的理由。47

=16=《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局部(图片来自 网络)
明末学者郭宗昌(?—1652)对钟铭的书写却极为赞赏,认为此书“古雅拙朴,在唐以上”,这种观点与清代部分学者的评述极为吻合48。对唐睿宗政治上的“不思反政”颇有微词。又说钟铭的“楷法兼篆分”实是《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的承续,但能“剂之以雅”,所以更胜古人。49清代学者大多认定钟铭的风格导源于《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虽不一定是沿袭郭氏的理解,但从时间先后而言,郭氏的论断自然可以代表较早学者们的普遍态度,影响清代后期诸学者的判断也是情理中事。然而以风格的相似性来判断书写风格的存续关系,往往存在论证的困难,既然不能有效论证,许多“定论”也就难免沦为空言。这也是书法史研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普遍问题。几代学者一齐将视线投向《李仲璇修孔子庙碑》,一方面或有将此碑影响力过度扩大化的可能,同时也遮蔽了后来者观察那段书写史的视野。欧阳修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某一时期的“风尚”,并承认其自身潜在的规律性。顾炎武认同钟铭书写中存留着可贵的“古意”,康有为也认为睿宗的书迹“古意未漓”,实出于初唐人“步趋隋碑”的具体实践50。顾堃对此大加挞伐,难免显露其故作惊人之语的动机和策略;刘熙载试图以“礼”调和自身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遇到的矛盾,这恰好与郭氏的“剂之以雅”相呼应,而郭氏的论述也正好衬托了刘熙载并不肯定的态度。
稍似古风:初唐书写风气的迁回递变
沿着前人的不同观点,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书迹,从中探寻杂糅诸体现象在睿宗时期的现实状况。近年来新出土的大量墓志,为全面审视初唐书写风气的迁回与递变提供了新的可能。
制作于唐贞观四年(630)八月的《□伯仁墓志》51虽然略显粗糙,但属典型的诸体相杂,尤具强烈的隶书意味。除第十一行“县”字以外,篆书结构基本上已经很少见,只存在于部分单字的构件之中。这类带有明显隋以前流风的书写,进入七世纪之后已经不多见了。诸体相杂的状态逐渐为稳定的楷书形态所替代。但从《□伯仁墓志》的情况来看,这种杂糅诸体的习惯并不能在短期内消失,只是不再像隋代那样流行。即使到七世纪中叶,偶然还能见到隋代遗风52,但从形式本身而言,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区别在于楷书笔意的主流化,篆、隶笔意和造型虽然杂错其间,往往都显得突然,不协调。墓志的制作在古代精英士人家庭生活中无疑是一件大事,它不仅作为社会富裕阶层的标志,也是纪念死者最重要的仪式53。这种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书写,从意义层面说,并不亚于服务于国家政治的碑刻制作。字体的选用,本身就象征着一种拥有文化的权利,他们习惯于使用比时下所流行的更为“古雅庄重”的书体。诸体杂糅曾为魏晋以降的流行体风貌,然而,对于初唐人而言,这已是过去的传统。随着楷书主流化的形成,唐人的生活也进入到全新的阶段,他们不再依赖过去而确立了自身的书写传统,这种“陈旧”的遗风也将随之消失。

=17=《口伯仁墓志》

=18=《郭懿墓志》志盖

=19=《郭懿墓志》志盖局部
篆、隶笔意与楷书的杂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七世纪中叶后,代而为之的是行、草与楷书的杂糅并用。立于咸亨四年(673)正月的《郭懿墓志》54虽然通体楷书,但其志盖却存在一个有趣的细节。唐代志盖的书写,大多依然沿用了之前带有装饰意味的花体篆书,也有少量的楷书。而这件志盖却出现篆、草杂合的现象,“唐故郭君墓志之铭”中的“郭”字以刻线双钩的草书呈现,感觉新奇而怪异。另外,咸亨五年(674)的《冯党墓志》55,楷书延续了隋代以来方阔、雍容的形态,曾经的篆、隶书已经完全替换成草书,譬如“之”“既”“秋”“明”“翦”等字。这反映出以行、草入志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标尚,也意味着墓主人是新时代文化的拥有者,并可以随意享用新文化所带来的便利。上元元年(674)的《李高墓志》56,或可视为这一“新风”开始转变的标志物,它既延续了隋代以来的书写习惯,同时又融合了新时期的形式符号。就其中“州”字而言,前后三次出现,用了三种形态:“潞州”作篆书 ;“仓州”作草书
;“仓州”作草书 ;“定州”作楷书
;“定州”作楷书 。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在隋代才出现,在更早以前的北魏就已经形成风尚,从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北魏寇臻墓志铭》拓本即可看出。《李高墓志》几乎集合了当时近百年内流行书写的符号特征,将行、草书代替篆、隶,变为一种新型的杂糅方式。相比更早以前的北魏,形式虽已明显改变,但这种趣味在墓志书写中的强化却始终如一。欧阳通书于唐龙朔三年(663)的《道因法师碑》57,其中许多横画末端上挑,有明显的隶书意味。这种笔意的残留,和墓志书写风尚的转变,恰好都印证了顾炎武“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遗意”的论断。墓志中行、草书的出现,正与上层社会碑刻行、草书入碑风气盛行的时间节点吻合。这恰恰反映了墓志书写对于研究时代书写风气的重要价值。
。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在隋代才出现,在更早以前的北魏就已经形成风尚,从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北魏寇臻墓志铭》拓本即可看出。《李高墓志》几乎集合了当时近百年内流行书写的符号特征,将行、草书代替篆、隶,变为一种新型的杂糅方式。相比更早以前的北魏,形式虽已明显改变,但这种趣味在墓志书写中的强化却始终如一。欧阳通书于唐龙朔三年(663)的《道因法师碑》57,其中许多横画末端上挑,有明显的隶书意味。这种笔意的残留,和墓志书写风尚的转变,恰好都印证了顾炎武“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遗意”的论断。墓志中行、草书的出现,正与上层社会碑刻行、草书入碑风气盛行的时间节点吻合。这恰恰反映了墓志书写对于研究时代书写风气的重要价值。

=20=《冯党墓志》

=21=《李高墓志》
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山西长治市城区南部的《唐故云骑尉李相妻徐氏墓志铭》58(见图24、25)。由麟德二年(665)十二月廿二刊刻的主体及景云二年(711)补刻两部分组成,补刻部分在志石下方侧立面,都是正书。从文字内容来看,可知李氏两位夫人相去四十六年先后离世,较大的时间差异及书刻人员的不同,导致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字得以同时保存。为我们展示了两个不同时代和政治背景下,在书写上所呈现的微妙变化。刻于麟德二年(665)的主体部分,基本可以反映武则天时代的书写面貌,尤可注意的是武氏改字及多处“诸体杂糅”的现象。其中“日”字作圆圈内凤鸟形符号,“年”作 ,“号”作
,“号”作 ,“之”作篆书体势
,“之”作篆书体势 。“都”字右部作“邑”形,而“部”“郡”右部都未变形依旧作“阝”。更可关注的是,“李”“一”“直”“二”“三”“上”等字长横都有明显的隶笔一味,在全然为楷书的字形上突兀地作此装饰,显然为当时某种群体自觉意识的反映。
。“都”字右部作“邑”形,而“部”“郡”右部都未变形依旧作“阝”。更可关注的是,“李”“一”“直”“二”“三”“上”等字长横都有明显的隶笔一味,在全然为楷书的字形上突兀地作此装饰,显然为当时某种群体自觉意识的反映。

=22=《北魏寇臻墓志铭》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另一值得注意的细节,《李高墓志》中三个“日”字,其中两个楷 书,另一则作篆书 。这一“日”字的写法,在隋代墓志中极为常见。如《田达墓志》(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王乾绪志》(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吴素暨妻樊氏志》(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丘志》59(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等皆属此类。《□丘志》中两个“日”字,圆圈中点画形状近似武则天所造新字中的“日”字。这些符号和武氏造字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联系,已经无从考证。但隋代某种文化现象在初唐的延续,以及这些奇异字形所带来的灵感,无疑成为影响武氏造字的一种社会因素。到七世纪晚期,楷书中夹杂行、草书的形式基本固定,篆、隶元素基本代谢完成。而这种“稳定”却在武周政权期间被打破,似乎将初唐经历短暂变迁后的新风貌很快退回到隋代的传统之中。进入八世纪的唐玄宗时代,这种篆、隶及异体字杂糅的风气逐渐消失,一段短暂而纠结的书写“复古”历程基本结束。当我们通过墓志——这一代表时代书写基底的重新审视,综合一系列现象来看,钟铭书写中的异体杂糅现象便不再奇异。它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典型的标本,昭示着个人在时代风气及政治压力面前的无奈随从60,尤其在武周政权之后的复杂格局面前,唐睿宗的因循与退让更能说明问题,钟铭的书写正处于这一关键的时刻。
。这一“日”字的写法,在隋代墓志中极为常见。如《田达墓志》(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王乾绪志》(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吴素暨妻樊氏志》(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丘志》59(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等皆属此类。《□丘志》中两个“日”字,圆圈中点画形状近似武则天所造新字中的“日”字。这些符号和武氏造字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联系,已经无从考证。但隋代某种文化现象在初唐的延续,以及这些奇异字形所带来的灵感,无疑成为影响武氏造字的一种社会因素。到七世纪晚期,楷书中夹杂行、草书的形式基本固定,篆、隶元素基本代谢完成。而这种“稳定”却在武周政权期间被打破,似乎将初唐经历短暂变迁后的新风貌很快退回到隋代的传统之中。进入八世纪的唐玄宗时代,这种篆、隶及异体字杂糅的风气逐渐消失,一段短暂而纠结的书写“复古”历程基本结束。当我们通过墓志——这一代表时代书写基底的重新审视,综合一系列现象来看,钟铭书写中的异体杂糅现象便不再奇异。它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典型的标本,昭示着个人在时代风气及政治压力面前的无奈随从60,尤其在武周政权之后的复杂格局面前,唐睿宗的因循与退让更能说明问题,钟铭的书写正处于这一关键的时刻。

=23《道因法师碑》翁方纲、李国松旧藏宋拓本(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 24=《唐故云骑尉李相妻徐氏墓志铭》

=25=《唐故云骑尉李相妻徐氏墓志铭》(局部)
三
为报先慈:钟铭的政治隐喻
嗣圣元年(684)武则天临朝亲政,不久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又立豫王为皇帝,自己仍临朝称制。此时的豫王即后来的睿宗李旦61。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追尊杨氏为“孝明高皇后”,改陵曰“顺陵”。长寿二年(693)加“无上”二字,曰“无上孝明高皇后”,又改陵曰“望风台”。随着武则天权力的不断集中,对其母杨氏连连追益,当她的政治地位进一步稳定后,遂将其父母的陵墓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作,并将其纳入为大周政权正名的一系列仪式与程序之中。《金石录》跋《武士彟碑》记载,武后追尊其父武士彟为无上孝明皇帝,为其陵墓立碑,“命李峤为碑文,相王旦书石”62。周晓薇通对文献的梳理,得出结论,目前所能见知的李旦书法碑刻著录大多是其为相王时所作。其中仅有《景云观钟铭》为“睿宗御书”,即其在位时所书。李旦作为“'唐时宗藩”子弟中少有的能书者63,被多次委任书写重要的碑刻,一方面因其素来善书64,同时或许也说明了李旦与武则天在政治观念上的融洽程度。65

=26=《口丘志》
武则天称帝以后,自载初元年(689)初至长安四年(704)末结束,历时十五年对部分文字进行了改造。共改十八字,先后分五次完成,其中“月”字历两次修改。施安昌认为,武氏这番“文字革命”的实质与其“恢复古代文字面貌”的说辞实在不符,其真实意义在于颂扬武周及自身政权的合法性。66她将“日”字改为“ ”,在圆圈内置凤鸟形态的符号,意象上正与当时“天命神凤,降祚我周”的社会舆论相吻合。而“月”字的两次改动,与其称帝后宗教政策的变化或有直接的关系,最初将“月”字改为圆圈中置“卐”字符,与其借《大云经》登基,大力宣扬佛教相配合。天授二年(691)三月,武则天颁《释教在道教之上制》,确立佛教在当时宗教界的领导地位。圣历元年(698)正月为调和当时的宗教矛盾,遂又颁布《禁僧道毁谤制》,强调两者“同归于善”与“皆是一宗”67。而“月”字的第二次修改时间正与此制的颁行同时,将其改写为“匚”与“出”的合体,这恰好可以说明武氏造字与宗教政策转变之间的微妙联系。
”,在圆圈内置凤鸟形态的符号,意象上正与当时“天命神凤,降祚我周”的社会舆论相吻合。而“月”字的两次改动,与其称帝后宗教政策的变化或有直接的关系,最初将“月”字改为圆圈中置“卐”字符,与其借《大云经》登基,大力宣扬佛教相配合。天授二年(691)三月,武则天颁《释教在道教之上制》,确立佛教在当时宗教界的领导地位。圣历元年(698)正月为调和当时的宗教矛盾,遂又颁布《禁僧道毁谤制》,强调两者“同归于善”与“皆是一宗”67。而“月”字的第二次修改时间正与此制的颁行同时,将其改写为“匚”与“出”的合体,这恰好可以说明武氏造字与宗教政策转变之间的微妙联系。
说起武则天借《大云经》称帝并大力宣扬佛教,或许与本文讨论的对象——钟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先从历史上著名的“明堂大火”事件说起。
唐初太宗、高宗时几欲建立明堂,却因“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而武氏则力排众议,不顾“诸儒”的意见,仅与北门学士们商议后,动用工匠数万人于垂拱四年(688)二月,摧毁乾元殿,并在原址建造明堂,当年十二月告竣,委僧怀义为整个工程的负责人。68
不难看出,武则天对佛教的信任远远高出那些受过正统儒学教育的朝中显贵——诸儒,他们虽是武周政权的强敌,但其意见在此时几乎完全失效。只有像薛怀义这样对武氏提供帮助的人们才能受到重视。天授元年(690)东魏国寺僧杜撰伪造《大云经》四卷,称武氏“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武则天得此伪经,立刻颁行天下,并在两京诸州同时建立大云寺收藏并推广《大云经》,参与伪撰和讲解的僧众此后皆受爵赐。69可见,武则天巧妙借助佛教的影响力及经文的社会功能,以制造舆论,巩固帝基。释教在武周的“革命”进程中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伪造《大云经》等一系列行为,为武则天作为女性皇权拥有者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供了宗教和精神上的支持。次年(691)四月,下制称“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天册万岁元年(695)正月,武则天精心营构的明堂遭大火焚烧。谁知一场大火竟无意成为武氏政治及宗教政策发生转变的引线,直接促使武则天在政治行为上,从倚重佛教向中国本土传统复归。事件发生之后,武氏“心不自安,言多不顺”,朝中群臣频频对其施加压力。于是责怪河内老尼不能预见灾情,遂将其及弟子遣散或杀害,又于瑶光殿前殴杀薛怀义。说明她已经感知到,佛教无法化解“明堂大火”给她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也不能为巩固帝基作出更大贡献,故而对佛教感到失望。从对河内老尼与薛怀义的抛弃,到697年四月在新修的明堂中铸造九鼎,再到久视元年(700)五月取消沿用七年之久的“金轮”帝号等一系列行为,充分表明武氏决定放弃“《大云经》的女身受记为转轮王的教义,全面向李唐旧传统复归”。70
景云元年(71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诏以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道集”。71这与武氏的《禁僧道毁谤制》相去十余年,但是两者前后呼应,正是沿用了武则天调和宗教、社会矛盾的方法。《隋唐五代经学学术编年》关于此事的考论认为:
自武德、贞观年间确立“道先、释后”顺序后,道、释之论争未有停息,但终此一政策从未动摇。武则天因特定的政治原因,遂于天授二年(691)重新调整三教秩序,诏令“释先、道后”,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睿宗认为僧道二教“理均迹异”,其社会作用皆为“拯人救俗”,若彼此互争高下,则“有殊圣教,颇失道源”,遂敕僧道“齐行并进”。此诏出后逐渐结束各教排次局面,并终唐一世,遂成定制。睿宗重论三教关系,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宗教问题,促进了三教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对于此后的思想文化格局影响深远。72
武则天时期受到打压的儒学,也在睿宗时期重新得到重视。景云二年(711)八月,“皇太子释奠于太学”。第二年(712)正月,睿宗亲自拜谒太庙,并大赦天下。且诏令“孔宣父祠庙,令本州修饰,取侧近三十户以供洒扫”。.次月,又“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并配享孔子庙”73。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与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存在明显延续性的同时,似乎表明了相比武则天更加明确的态度:
则天天授三年,追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则天长寿二年,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停《老子》。神龙元年,停《臣轨》,复习《老子》。以邹、鲁百户封隆道公、谥曰文宣。74
武氏对于三教的态度,可从上文推想她那纠结不定的心态75。有学者认为,睿宗的政策变化结束了各教之间相互排异的局面,乃至终唐一世,逐渐称为定局。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还当在下文继续讨论。
嘉庆间浙籍诗人金衍宗曾作《唐景龙观钟铭拓本》一诗。通过眼前的拓本,金氏将视野向整个历史空间延展,并敏锐地觉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冲突:
天堂神宫拜圆册,铜匦金轮置庭室。阿师血像高百寻,未有淫昏不佞佛。斗南一人忠回天,鹉翼双垂幸未折。乐章旋奏桑条韦,晨牝当阳甘覆辙。猖狂但乞二氏灵,慧范崇恩并加秩。帝后争营佛寺新,观亦落成景龙日。莲台瓔珞月双圆,椒殿衣裙云五色。至尊惨继东宫戕,仙佛几曾裨毫末。景云反正由平王,冥助何关法善术。金仙玉真秾如华,两两黄紽改妆抹。铸钟作铭帝观书,楷法犹从八分出。铭辞骈俪踵齐梁,起草知经谁手笔。得无昭容秤量余,鬼蜮风流巧涂泽。佛耶仙耶安可诬,地狱正为是人设。76
“帝后争营佛寺新,观亦落成景龙日”是金衍宗对武、韦时期帝后争相营建寺观这一奇怪现象的描述。他发现,当时的皇室成员几乎都“淫昏”而“佞佛”,而且在很早的文献中就已经总结了此事给当时的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负担:
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77
皇室成员沉溺佛教与恣情奢纵,一直都是有识之士劝诫的对象。又如久视元年(700),武则天继明堂大佛之后要铸造大佛,想让“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得知,立刻上疏劝谏:
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78
又说:
游僧一说,矫陈祸福,翦发解衣,仍惭其少。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纳妻,谓无彼我。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子制敕。……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维,实所悲痛。79
狄仁杰一番话,直接指出了当时因过度崇尚佛教而给国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80,字里行间都透露出狄氏对这种政治隐患所感到的忧虑。这一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权力的滥用及佛教在当时的盛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排挤与争斗。唐中宗在位期间,韦嗣立劝止营构寺院,认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81韦氏所见,与狄仁杰同出一辙,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然而,唐中宗并没有因韦氏的劝告而停止相关的活动。
景云元年(710)睿宗在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及诸臣的拥立下,重新登上皇位。是年十二月,睿宗“资天皇太后之福”,让女儿金仙、玉真公主出家为道士,以方士史崇玄为师82,预备在城西为其二人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建议道:“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劝谏无果,又于次年五月,坚持为女儿造金仙观和玉真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辛替否、魏知古、李乂等人上书极谏。睿宗虽执意不从,却又十分认同朝臣们的“切直"。83 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睿宗一方面执意建造宫观,同时又努力地维持其与朝臣之间的关系。辛替否等人纷纷就此展开批评,认为皇帝竭力营造寺观是迷心于释、道的重要表征,他们害怕武后及中宗时代的回返,希望睿宗能够将失败的历史引为前车。通过考察因睿宗筑观而产生的巨大阻力,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这一时期各方政治势力的相互竞合。后来,不知迫于何种压力,睿宗还是下发了《停修金仙玉真两观诏》,并对营造二观的缘由作了权威的解释:
朕顷居谅暗,茕疚于怀,奉为则天皇后东都建荷泽寺,西都建荷恩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京中造观,报先慈也。岂愿广事营构,虛殚力役。84
我们知道,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上阳宫驾崩之后,朝廷又经历了一系列内部政治斗争。虽然睿宗得以重新登上皇位,但他内心的不自信以及对武则天威严的芥蒂之心不可言表。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及复杂的政治局势面前,李旦表现出一贯的退避与谦让之风,甚至将居丧期间那种哀怨与孤独作为一张感情牌亮在群臣面前。不久,他又突然表示希望将政事尽快移交给太子李隆基,以申明其素来淡泊的本性。景云二年(711)四月,李旦召见三品以上朝臣,并对他们说:
朕素怀淡泊,不以万乘为贵,袭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85
对于皇帝这番自诉,群臣无言以对,分别代表太子和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们的态度存在微妙的差异,太子这边语焉不详,而公主这边却是严肃地反对,这样的回应无疑为睿宗的心理带来更大的压力。事后睿宗即将政事交与太子处理,而皇位尚没有交接。此后,睿宗一心要建造宫观,依然遭到多位朝臣的极力反对,只侍中窦怀贞“独劝成之”且亲自督工,窦氏明确的态度与积极的行为自然离不开太公主的支持。86而此时与太平公主势力相当的太子李隆基在释、道问题上的态度一直不甚明朗。在这样的政治张力面前,无奈的唐睿宗只好将则天皇后引以为保护自身的说辞。睿宗一再强调,他在东西两京修建菏泽、荷恩两寺,以及让金仙、玉真两位公主出家并为之修营宫观,全然是出于对武氏的孝德,这样的解释对于稳定当时的局面显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有朝臣在反对营建宫观的奏疏中,也将睿宗这一动机视为“尊德敬道”的具体体现87,虽如此,此事仍因“欲益反损”而遭崔莅等人的劝阻。睿宗深惭外议之“不识朕心”,又实因“书奏频繁”而不得已停止工程。但代表着其与武后政治关系的筑观行为的初心却不能就此改变,他决定在别处建造,也“不劳烦百姓”,并警告群臣:若尚要干忤则“当寡于刑”。88
从各类史料来看,武后、中宗在位之际,宫殿及寺庙的营建达到了异乎寻常的奢侈,穷极壮丽的建造风习成为政府及百姓最大的经济和劳役负担,帑藏为之空竭。正所谓“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己,则天在位,已绝缀旒,韦后司晨,前踪覆辙”89。中宗复位之初,袁恕己害怕“素以工巧见用”的杨务廉“更启游娱侈靡之端”,于是进言中宗以阻止其任用,他说:“务廉致位九卿,积有岁年,苦言嘉谋,无足可纪。每宫室营构,必务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广昭圣德?”90可见到中宗时期,朝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帝后争营佛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将其视为有碍发扬“圣德”的不良作风。在这样一种舆论氛围下,睿宗再造宫观便成为逆于时势的覆辙之举,遭到诸臣的反对当为自然之势。睿宗此刻既不能完全回避唐廷崇尚奢靡的一贯风气,又不能与当下的新兴政治群体形成对立,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而看到未来的世界。91在这些前提下,诏书中“报先慈”的说法显得意味深长。
景云二年(711)九月,睿宗在中宗造好的景龙观中重新铸造这口大钟,在其铭文中首先强调,由中宗所建的景龙观十分壮观,虽“名在骞林,而韵停钟虡”,重铸大钟以实“钟虡",是为重建国家礼制秩序的象征92,这是政权回归李氏之后的新风气最合理的表述。睿宗知道,铸造景云钟一方面不会因财力的过度消耗而招致外议,同时又可以达成“悬玉京而荐福,侣铜史而司辰”的政治效应;既能向外界表达其兄弟二人前赴后继兴复朝廷、重建秩序的决心,也可以通过这一举动追念自己的母亲,同时又能满足其对于音乐的喜好93,这样一来,景云钟的铸造巧妙地成为调和各方矛盾的媒介。在他撰写的铭文中,还不忘铭记祖宗的荫德及广大百姓的资助,又因玄宗与睿宗一样,素来喜好音乐,虽然铸钟与筑观同出一时,但并未被阻止,不能不说与这一背景有重要的关联。相关文献显示,第二年七月睿宗以“高居无为”为理由,将皇位传于玄宗李隆基,自此以太上皇的名义逐渐淡出政治舞台,闹得沸沸扬扬的筑观事件也随着景云钟洪亮悠远的声音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唐睿宗留给历史的,是看起来柔弱谦让而又面面俱到的形象,还有这件精美的皇家重器及数百世争相流传的书刻精品。在它们的背后,或许隐藏着种种难以言说的苦痛。这种苦痛,可以从睿宗处理宫廷内部的政治博弈,以及与朝臣们周旋的过程中感受到几分。
通过文献记载得以将远去的历史事件勾勒还原,而镶嵌于期间的艺术作品或者碑刻、建筑,都有可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历史的真相。一件碑刻背后,往往蕴藏着一段复杂的生成史,在生成史背后又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及文化内涵,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94 如此,唐睿宗的《顺陵碑》和景云钟铭也是如此。唐睿宗并未完全放弃母亲的一系列宗教政策,看起来虽然有所改变,实际上则一以贯之。只是受到新时风和士风的影响,睿宗不得不做出退让。金仙、玉真二位公主的宫观虽然受到舆论压力而不得不停止,但崇尚道教的实际行为却没有因此改变,景云钟的铸造及钟铭的镌刻,更加强化了武则天晚年偏好“长生久视之术”95,及睿宗借“报先慈”之名推行其宗教政策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于纵情宴乐,并在政治面前难以取舍的睿宗形象。至于结束各教之间相互排异的局面,实非睿宗真正的主观诉求。
余论
1827年,顾广圻(1770--1839)将新得到的《顺陵残碑》拓片自苏州寄给远在北京的龚自珍,龚氏获得此拓,喜出望外,所以赋诗二首回赠。顾氏与龚自珍交往颇深,两人又均爱金石收藏,常常相互赠酬。96这次馈赠对于龚自珍来说似乎意义重大,此前他认为“南书无过《瘗鹤铭》,北书无过《文殊经》”,因为《顺陵残碑》的到来而使他的藏品体系得以完善。他说睿宗是唐代帝王中的“书圣”,并将其书迹看作合成南北书风的“唐型”代表,97 这是关于唐睿宗书写最具历史意义的总结式评价。而厉鹗在金农那里看到钟铭拓本之后,也曾题诗一首,更加关心钟铭背后的政治隐喻98。他认为,历史虽然已经来到睿宗的时代,但武则天的影响尚未过去,因政治变革而受苦的“寒饿”百姓并不像钟铭的“雄词”所描述的那样美好。因为几代政治高层在宗教政策上的反复,导致国家政治的混乱,在帝王必要的丰功伟绩面前,“虚无”的道教岂能如此被重视。面对钟铭拓本,厉鹗感慨睿宗铸造景云钟并题写钟铭实是歌颂和传播那些虚无的功绩99。从史载来看,睿宗的政治生涯可谓坎坷,他的进退始终处于多种势力竞合的复杂局面中,在这种复杂局面中,他选择退让以保全自身。睿宗建道观,朝中大臣纷纷抗议,却得到了太平公主的支持;看起来有拨乱反正,并将宗教、文化政策向唐代本土文化靠拢的意义,但实际却卷入了身不由己的政治斗争。欧阳修早已批判过武则天对唐代政治秩序的破坏,甚至认为武氏就像“毒流”一般祸害天下,其书迹也当为唐人所遗弃。因为武氏的宗教政策所带来的危害100并没有在睿宗时期得到改善,睿宗“侧耳不闻雷霆”101的消极政治态度成为史学家们反复批评的对象。尽管如此,他仍然将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那些如厉鹗批评的“虚无”的功绩之中,且笃好音乐,崇尚道教,沿袭筑观、刻铭等夸尚奢靡的前代遗风。
钟铭虽未必是睿宗亲笔,但这件作品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因睿宗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而备受冷落。他的书写风格既不是完全的隋代风习,也没有太宗时代遵从“二王”的具体影响,更多形式上的特征来自“复古”的所得。他在武氏政权前期有意回避李唐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无意地将心力投注到初唐以前的传统。所以,睿宗在“古意”和时风面前始终保持着“纠结”的心态,一方面保持与武则天的联系,但又期望在政治上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张力的作用反映到书写上,可以视为总结并中和了唐初以来的各种风格,并开创了中唐以后“肥厚雍容”的新风尚,这股新风对宋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02。关于钟铭深刻的历史背景及其与书史的关系,还望有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学识谫陋,只能略做试探。